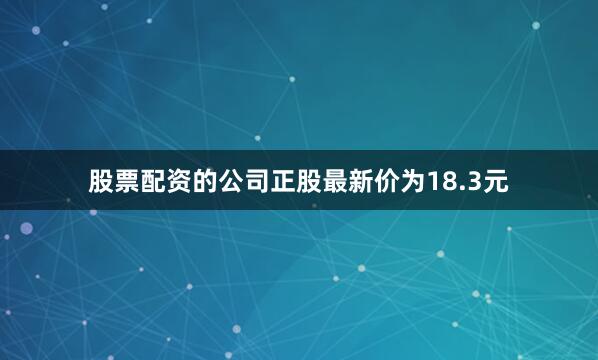长春将成死城!
“长春必成死城!”
一、将长市周边五十里划定为封锁地带,区域内除军事必需物资外,应严格限制人员与车辆、马匹的自由出入。若确有特殊情况需通行,各县政府有责任制作并发放通行证与居留证给民众(军队人员外出时,通行证由团部负责签发),以便在查验时作为有效凭证。
自总部发布断绝与长春市商业往来的公告,并严格禁止粮食、柴草等生活必需品流入长春之后(公告源自总部发布),对任何企图走私上述物资越境,意图援助敌方的个人,一经查获,将立即予以扣留,并移交相应机关处理(地方物资由县级机关处理,军队物资则由团级机关负责)。但若携带有效证明文件,且所运物资系流向本区域,则必须予以放行,不得无故延误。对于任何借机敲诈勒索或未依规定程序执行没收行为的,必须依法进行严厉查处。
三、考虑到敌方所实施的抵制人口疏散的策略,对于试图离城的民众,我们必须采取有力的拦截措施。针对那些意图返回的个体,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加以阻止,以防止敌方城市人口实现大规模、快速的撤离,进而加剧其粮食供应的紧张局势。然而,必须严格命令部队,对于出城的人民,仅应运用劝阻手段,严格禁止使用任何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和开火。
四、为确保上述封锁措施得以有效执行,必须在各条道路的出入口设立检查站点,并实施严格的盘查与警戒。除军队负责执行外,还需广泛动员民众参与守望与警戒任务,以防止敌特、奸商及反动分子趁机作乱。具体警戒与盘查的详细规定,将由当地驻军与地方相关部门共同制定。
五、敬请居住在封锁区前沿的朋友们留意,请将多余的粮食及暂时不用的物资妥善存放在地窖内,以避免遭受敌方的不义掠夺。
为确保长春城实施严密封锁,东北局迅速作出部署,特派萧劲光与萧华同志担任指挥重任。6月初,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前线围城指挥所正式成立,萧劲光同志担任司令员一职,萧华同志则担任政治委员。15日,萧劲光与萧华同志在吉林市召开师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东北局的战略指令,并对围城作战计划进行了细致的调整。会议决议,一纵队和六纵队撤回进行休整,而由十二纵队的第三十四、三十五师,六纵队的第十八师,以及第六、七、八、九、十共五个独立师和一支炮兵部队组成围城的主力,负责接管并巩固防线。22日,围城部队按照既定计划进驻指定阵地,自此对长春实施全面的封锁行动。
长春,东北地区的繁华明珠,曾是伪满洲国的都城,其常住人口一度膨胀至六十万以上。随着抗战的胜利,尽管人口有所缩减,但仍有五十余万居民留居于此。然而,1946年5月,国民党军队接管长春,随之而来的城市动荡令居民纷纷离城避难。北满地区的地主豪绅及伪满官员,纷纷逃离解放区,涌入长春寻求庇护。至1948年初,长春的居民人数急剧减少至四十万,其中十万人属于国民党军队及其眷属以及留守人员。我军在解放四平之后,切断了长春与沈阳的交通联系,长春城内恐慌情绪蔓延,新一轮的逃亡潮再次掀起。富有家族与国民党空军眷属纷纷乘机逃离,而普通民众则选择了徒步,在我军围城之前,长春城内的居民约有一半已经逃离。
我军实施封锁后,城内迅速作出反应。据东北野战军总部的《阵中日记》所载,自6月1日至5日,敌方飞机每日均有十余架次向长春敌军空投补给,每日投掷的米面累计达数百包。“长春难民,每日仍有二、三百人经孟家屯外逃。大孤榆树难民因粮食告罄,竟至抢夺我警戒部队的粮食。”总部于5日发布命令,要求“六纵派遣一个营前往孟家屯执行封锁任务,并派遣得力干部进行监督,严禁长春居民外出,以缓解粮食压力。”同时,命令一纵利用远程炮火摧毁敌军在城内新皇宫设立的临时机场,阻止敌运输机降落。至7日,六纵再次下达命令,强调“部队需摒弃片面群众观念和同情心,以免影响封锁任务的执行和敌人的歼灭。”
长春之敌不甘束手就擒,屡次派遣小股兵力出城劫掠粮草,同时对我国的防御阵地实施干扰。6月16日,洪熙街的敌军一个营部采取三路并进的方式,对我18师孟家屯阵地发起猛攻,然被我军英勇抗击,挫败敌军企图。至23日夜间,一股敌军于八里堡一带向我独立8师阵地发起攻势,亦被我军果断击退。7月7日,长春守敌调集约四个团的兵力,在炮火掩护下分三路发动进攻,激战至午后,最终被我独立6、9、10、11师紧密联合防守,成功击退敌军。城内粮荒严重,导致粮食走私活动猖獗。6月18日,一纵报告指出:“在长春八里堡周边,夜间每天都有五六十人前往卡伦采购粮食,他们经由野外小径,用麻袋将粮食背回长春周边。”22日,六纵报告提到:“部分民众趁夜间警戒空档,将粮食偷运入城。22日晚,18师的一个排在田家油房及广播电台附近,截获了偷运的六麻袋粮食,每人背负约30斤。”24日,18师报告指出:“孟家屯至八七病院一带警戒有所松懈,民众利用夜间通过河沟、荒地偷运粮食。我们的应对策略是:在黄昏至半夜间加强流动哨巡查,并在必经小路布下埋伏,每晚可没收数百斤粮食。”
02、堵漏,严封
“我们派遣专人进行定期巡查,以保障封锁线的安全,并协助地方党组织和政府动员周边民众实施坚壁清野的策略,严厉打击那些企图将粮食非法运入城内的违法分子。”自此,粮食走私的现象得以彻底根除,长春的封锁线也因此变得更加坚固可靠。
当长春陷入困境之际,郑洞国早已未雨绸缪。自三月初接掌重任,他敏锐地预见到解放军即将形成的包围态势,于是提前储备了充足的粮食。从三月底到五月底,他积极动用东北流通券,指示新七军、六十军以及保安旅自行采购粮食。新七军原驻长春,根基深厚;而六十军则是新到任,需即时购买。郑洞国下令国民党长春市长尚传道协助筹措军粮,尚传道立即指令吉林省粮政局与长春市田粮管理处代为采购,在短短两个月内成功储备军粮约三百万斤。长春市政府还需兼顾八千名职员与警察的生计,尚传道便将南京政府寄存的百万斤大豆购入,以此作为市政府的粮食储备。
四月之际,郑洞国委派尚传道全权负责,对全市居民进行户口清查与余粮登记,以期全面了解我市粮食储备状况。据当时统计数据显示,我市常住人口与现有粮食储备仅能维持至七月,八月之后,粮食供应将面临严重短缺。
5月24日,解放军成功夺取了大房身机场,并迅速对长春形成了严密的包围。随着粮食供应几近断绝,每日的食量急剧减少。面对这一紧急关头,郑洞国向蒋介石紧急求援。蒋介石于6月初回复了两封电报。一封是充满激励的公开电文,他写道:“我对你们和全体士兵,就如同对待自己的亲兄弟一般,我时刻铭记你们的辛勤付出。但若未做好充分准备,增援部队在行进途中可能会遭受重创。希望你们能够坚持不懈,全力支撑。”另一封则是秘密电报,指示郑洞国将长春市内的粮食和物资全部收归公有,并禁止任何私人交易。政府将根据人口数量进行粮食的分配。在这封电报中,蒋介石“杀民养军”的意图暴露无遗。
郑洞国火速将尚传道召集至面前,共谋对策。尚传道立刻坚定地表达了反对意见:“当前局势下,我无法保证市属人员不会出现贪污勒索的情况。一旦实施,必然引起极大骚动。若您执意执行电令,请派遣新的市长,我实在无法胜任这一重任。”紧接着,他补充道:“所谓尽收物资、按人口分配粮食,无论是否实行,最终也只能支撑到7月底。8月份过后,粮食供应将告竭。”郑洞国深思熟虑后,表示可以暂缓执行该命令,但必须制定一套粮食管理措施。经过一番讨论,他们共同拟定了一份《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了民众存粮的最高限额,确保其能维持至9月底。多余的粮食,按照政府规定,须将一半卖给政府作为军粮,其余部分可在市场上自由交易。粮食交易必须遵循政府定价,严禁哄抬物价。对于违反规定的,将进行严厉惩罚,直至极刑。
粮食管制令一经发布,却未能有效稳定局势,反而激起了民间的焦虑情绪,粮价犹如脱缰野马,一路狂飙。我军侦察数据显示,高粱米的价格呈现令人震惊的涨幅:6月2日为4万元,6月23日飙升至22万元,7月14日更是高达80万元,7月28日进一步攀升至330万元,8月1日达到720万元,8月18日更是飙升到2300万元,而到了9月10日,价格已高达2800万元(东北流通券)。面对失控的粮价,初期尚传道还曾派人前往市场,意图抓捕投机者,以儆效尤,遏制投机风潮和黑市交易。然而,在一次行动中,警察逮捕了三名故意哄抬价格、抢购粮食的商人,经查实,他们实际上是受保安司令部委托购买军粮。此事最终波及到郑洞国,幕后黑手竟是副司令李寓春,他涉嫌与粮商勾结。尚传道向郑洞国汇报此事后,要求严惩。无奈之下,郑洞国只得同意将三名商人处决。然而,随着新7军人员也卷入粮食投机,郑洞国倍感愤怒,尽管部下屡次求情,他还是将一名新7军的军需官处决。但对于上层军官的不法行为,他却不敢深究。
“为国家舍身献命,换取一餐温饱,实属无愧。”面对众人的愤怒,郑洞国亦感束手无策。
饥民挣扎生死线
全城军民不仅饱受粮荒之苦,就连日常做饭取暖的柴禾燃料也濒临枯竭。昔日,国民党军队撤退入城,沿途强行将百姓屋顶的茅草掠走,运回城内。然而,即便这些物资也难以维持数日。面对60军的燃料需求,得到的答复却是“自行解决”。新7军虽有余粮,却坚决拒绝支援60军。在无奈之下,60军的士兵只得拆毁房屋,首先拆除了无人看管的公共房产——那些日本侵略者留下的建筑,城南的满映公司(如今的长春电影制片厂一带)成百上千的楼房,很快沦为废墟。公共房产拆尽后,他们又转向民房。无人居住的空屋、全家人亡故的破旧老屋,无一幸免。一座三层楼房,先是拆掉屋顶,再将房梁烧毁。住在三层的居民被赶到二层,二层的人又被赶到一层。最终在拆除二层时,居民们被像赶羊一般驱赶。情急之下,百姓们也纷纷上前抢夺木材,与士兵发生混战,甚至有人开枪伤人。军官无力制止,只能任其发展,以至于整条街道、整个区域都被拆得面目全非。公园和路旁的大树被砍伐一空,墓地中的棺材也被挖掘出来。最后,甚至将大马路的沥青路面挖开用来烧火。长春这座曾经美丽的城市,就这样被破坏得千疮百孔,景象凄凉。
04、国民党驱逐民众出城
“恰逢七月一日,毛泽东同志的寿辰之际,八路军在城外设下关卡,以此诱使民众外出。民众在出城途中,遭到警备司令部人员的逐一盘查,随身携带的粮食被悉数没收,身份证亦被扣留。一旦跨过国民党的关卡,民众便再难返回。”
05、林罗围城报告
“竭尽全力,鞠躬尽瘁。”士兵们纷纷表示:“八路的策略真是高明至极,不如早点行动为妙。”
面对敌军的围困,我方果断实施了强制性的疏散计划,其目的是为了减轻压力,并便于对剩余粮食资源进行控制。具体策略包括恶意操纵粮价,疯狂抢购市场中的粮食,以此迫使市民离开城市。同时,我们实行粮食管制,对每个人的粮食储备进行严格审查,若其储备不足三个月之需(每人每月应储备45斤粮食),便予以强制驱逐。在街头拘捕饥饿的乞丐,释放狱中的囚犯,并将那些无用的军官、职员、伤病员、残疾人、军属以及学生等人员疏散。被疏散的民众通常会携带证明文件,以便前往沈阳进行登记。与此同时,我们还对市民进行了误导,声称“7月1日是毛泽东的生日,八路军将撤除关卡”,或者以发放粮食为名集体驱逐,甚至组织工人和学生向我们请愿,甚至有大量难民向我们哨兵涌来,使得我方难以有效应对。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我方采纳的核心策略是实施严格的封锁措施。在第一道防线,我们部署了哨兵,并配备了铁丝网和战壕,确保接合部无缝对接,彻底堵塞所有缝隙,防止难民外逃。对于试图外出的人员,我们采取了劝返政策。起初,这一策略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饥饿问题愈发严重,饥民们在夜以继日地成群结队涌出,即便被我方驱赶,他们仍聚集在敌我警戒线之间的中立地带,导致大量饿殍横陈。仅以城东八里堡为例,死亡人数便高达约2000人。至8月初,我们适度放宽了封锁,三天内共疏散了2万余人。然而,城内的难民迅速被疏散,数万人又迅速占据了这一空缺区域。此时,市内高粱的价格从700万跌至500万,封锁解除后价格又迅速回升至1000万。因此,在封锁战中,我们必须坚持基本禁止出入的原则,对于已经外出的难民,应酌情分批次、陆续释放,而非一次性或大量释放,以免敌人能在短时间内迅速疏散。若完全不放行,将导致饿死人数激增,后果不堪设想。
“严格禁止饥民出城,对于已外出者,亦需竭力阻止其返回。在此过程中,对饥民和战士均需耐心进行说明。随着围困日子的延长,部队中急性病症病例逐渐增多。有人质疑我方围困的原因是力量不足,还有人认为长时间的围困并无实际效果,敌军可以通过空运获得补给,因此呼吁我们迅速发起攻击。针对这些观点,我们主要阐述长期围困的必要性,并利用逃兵之口描述敌方所遭遇的困境,逐步提高敌方对围城战的认识。目前,敌方正在进行恶意的宣传,诬称我方意图饿死长春市民。而我方则通过释放难民并实施救济的事实,揭露敌方抢夺粮食、制造饥荒,企图驱逐市民的阴谋。尽管被释放的难民对我方仍持有不满,但经过我们的救济,他们的态度相较于之前已经有了显著的转变。”
06、杨滨谈民困
应对那些因国民党驱逐而被迫滞留在敌我哨卡交错地带,俗称“真空区”的长春民众,是我党群众工作政策中的一个关键议题。当时,部分部队在执行政策时出现了偏差,仅允许携带枪械和军用物资的人员通过,这一做法引发了诸多混乱与不便。针对这一情况,负责长春外围敌对工作的杨滨(又名杨重,曾是潜入60军的地下党员,担任过曾泽生的副官长。1947年初,他脱离60军转投我方,并在推动60军长春起义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者注)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些问题,随即向上级领导提交了一份详尽的情况报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建议。
他们无视民众福祉,执意将大批贫民赶出关卡之外。对这些困苦的百姓,他们声称:“共产党是你们穷人的代言人,你们快去寻找共产党吧。”对于粮食仅够三个月的民众,他们采取各种手段进行驱逐,手段或是强制或是虚假宣传。比如,在共产党的生日——七一之际,他们谎称关卡将开放三天,以此诱骗出数万名民众;在毛主席的生日——八一之时,他们又宣称将实施三天大赦,再次骗走数万名民众。在民众走出关卡之时,他们擅自收走身份证,从此无人能够重返。
杨滨继续笔锋,沉痛地写道:“那些无家可归的民众渴望踏入我们的卡哨寻求庇护,却同样遭遇闭门羹。于是,成千上万的难民被困在敌我之间的缓冲地带,饱受饥寒之苦,饿殍遍地。若此困局持续下去,长春的普通民众恐怕将无一幸免,尽数饿死。而那些手中尚存少量粮食的中上层地主和资本家,却得以苟延残喘。届时,我们前往长春进行救济的,恐怕也只有这些地主和资本家。即便他们接受了我们的援助,心中仍旧充满敌意。我们提出这一问题,并非仅仅出于仁慈,而是关乎我们是否真正需要这些百姓。国民党反动派对百姓冷漠无情,甚至将贫苦百姓驱逐出卡哨之外。同样,我们绝不允许他们进入,任由他们在两卡哨之间饿死。这一点,确实值得我们深思熟虑。”
(1)此计旨在在长春市内制造混乱与恐慌,以加大敌方作战的难度。(2)预期民众因饥饿难耐而爆发抗议或暴动。但敌方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手段,将城内受困于饥饿的贫民驱逐至城外,设立关卡。实际上,这一举措并未给敌方带来太多额外麻烦。相反,敌方实施了高物价政策,大幅提升粮食价格,将粮食资源搜刮一空。此举迫使民众不得不离开长春。至于市民的抗议或暴动,长春市敌方兵力约10万人,而市民总数约50万人(现已有所减少),其中女性占半数,还有众多老弱病残。换句话说,长春市的青壮年人口仅约10万人。因此,指望这些手无寸铁的民众与装备精良的十万武装部队抗衡,实乃痴人说梦,这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1)对于真正的难民,应实施恰当的安置与援助,并开放通道使其得以进入解放区;同时,设立专门的难民收容区,确保有组织、有计划地接纳他们。(2)明确规定,携带武器或军用物资的人员(军人除外)不得作为进入解放区的资格,并设立相应的奖金激励机制。
07、林罗安置难民
萧劲光、萧华、陈光、唐天际、解方等同志,特向第十二纵队、吉林军区以及辽北军区呈报军委:
自即日起,所有滞留城内城外的难民同胞,应即刻启动疏散流程。对于有意愿离城者,应无条件保障其通行自由。鉴于长春市粮食储备已告急,若不迅速疏散,将使众多市民陷入饥饿的威胁。敬请各界据此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务必分阶段且迅速推进,确保在十日内完成疏散任务。对于选择离城的难民,需调动地方党组织和军队的力量,全力以赴开展救济与慰问工作,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病弱、残疾者,提供人力和马车的援助,确保其安全抵达目的地。首要任务是就近各县分批进行疏散安置,并动员群众提供援助,确保难民离城后生命安全,降低伤亡,以此挽回不利影响,赢得民心。对于那些混入难民中的特务,必须严格排查并予以扣留;对于敌方官兵,则应统一收容,送往吉林解放团接受训练。对于中学二年级以上学生、技术人员和专家等,应积极争取他们来我区服务。此次开放难民出城,并非为了解围长春之敌,围困敌人的工作仍需持续进行,绝不可有丝毫松懈。关于防止敌人利用秋收期间抢夺粮食,以及组织军民抢收抢割等事宜,应严格按照兵团指挥部的计划加紧执行,并将执行情况及时电告。
林、罗、高、刘、谭、周
9月11日
接获命令后,萧劲光等人迅即传达指令至各纵队及独立师。封锁线的哨卡随即解除,饥饿的民众如潮水般蜂拥而出。十二纵队向上级报告称:“自15日起,朱家崖难民开始有序放行,每日释放5000人,十天内总计5万人。若每日释放2万人,则需耗时25天,预计18天即可完成。至14日晚,已释放3000余人,并缴获轻机枪一挺。”为妥善安置这些难民,围城指挥部与地方政府紧密协作,在前线与后方设立了数十处规模各异的收容所。从“真空地带”逃出的民众因饥饿过度,一见到米饭和馒头便狼吞虎咽。然而,由于肠胃过度虚弱,不少人因胀气而命丧黄泉。汲取了教训后,收容所决定在初期仅提供稀饭,随后逐步增加食物的分量。在整个围城期间,难民委员会共发放了4000吨救济粮、500斤食盐以及6亿元救济金(东北流通券),成功将众多濒临死亡的饥民从死亡线上拉回。待难民们身体康复后,干部们将他们一批批疏散至长春城外的乡村,并迎接下一批从城内逃出的难民。尽管如此,围城战仍在激烈进行,长春城内人去城空,但饥荒的状况并未得到丝毫的缓解。国民党军队试图将负担转嫁给我方,却并未从中得到任何利益。
08、死城长春
自7月份起,饥饿的尸骸开始在卡哨内外随处可见。至7月下旬,市区居民的家中粮食已然耗尽,不得不依赖豆饼、酒糟来勉强果腹。然而,进入8月,连豆饼、酒糟也开始变得日益稀少,到了9月中旬,这些食物资源已经彻底消耗一空。尽管正值中秋佳节,长春北地的树叶已纷纷落满地,饥饿的人们只得纷纷捡拾树叶用以煮食,以求苟延残喘。警备司令部督察处的院落及其周边,本应是绿意盎然之地,但那时,每天都有许多面黄肌瘦的孩童,成群结队地在围墙四周争抢树叶,而那些特务头目们却认为此举有失体面,竟下令哨兵驱赶,甚至动用枪械进行威胁。然而,这些手段并未能制止他们的行动。到了9月上旬,更是发生了令人发指的卖人肉惨案。
自8月1日强制疏散政策实施以来,卡哨内外地带因饥饿而导致的死亡人数持续攀升。饿殍遍野,白骨如山。洪熙街、二道河子等地的卡哨内外,尸体横七竖八,哀嚎之声不绝于耳,仿佛人间炼狱。直至10月19日长春解放,人民政府入城后,经过精确统计,因国民党“杀民”政策而饿病身亡的长春市民累计达12万人。人民政府接管后,在卡哨内外地区共掩埋尸体约8万具。卡哨以内的居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亲人丧命,这实乃空前绝后的惨绝人寰之灾。
十二万生命瞬间凋零,这一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远远超出了辽沈战役期间敌我双方的伤亡总和。根据战役结束后的统计数据,我军共计伤亡67339人,其中阵亡者高达14010人。尽管国民党军被全歼47万人,但其伤亡人数仅为56800人,且被击毙者不足总数的一半。
谁应负责12万民众之死?
“岁月流转,每当我回顾长春围城那一段惨痛的历史,心中仍不禁泛起阵阵惊悸。长春人民所经历的深重灾难与巨大牺牲,让我深感无尽的痛楚与愧疚。此生此世,我似乎都无法向长春的父老乡亲们交代清楚这一切!”
作者简介:
刘统,1951年9月1日诞生,2022年12月21日离世,为我国汉族男性。他于京城降生,后于山东大学历史系圆满完成学业。在文革风云激荡之际,刘统成为备受瞩目的“老三届”杰出代表之一。他拥有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供职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担任研究员,并荣膺大校军衔。同时,他还身兼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以及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的教席。
a股怎么加杠杆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在线配资炒股脚步也比之前更加灵活
- 下一篇:没有了